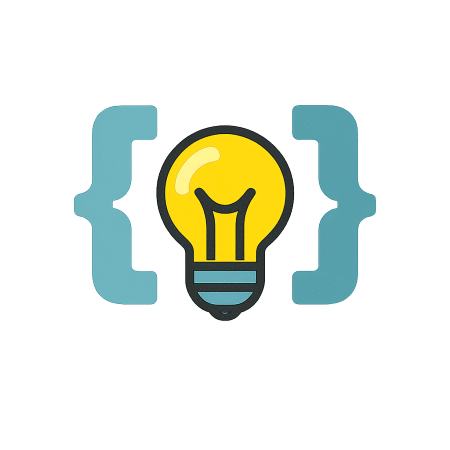今天是汤总初一的第一天。
早上6:30叫醒他,6:55吃完早饭,背着书包独自出门去坐地铁了。
昨天已经报到并适应了一天,今天终于可以自己上下学。家门口就是地铁站,四站路,从出门到校门口,全程不到半小时。对住在地铁沿线的家庭来说,这已是莫大的便利。而那些不在地铁覆盖范围的家庭,往往得更早出发——要么骑电瓶车送到学校,要么送到地铁口再换乘。
说到电瓶车,我带汤总出门从不骑。倒不是怕麻烦,而是实在不放心。
我们俩加起来三百来斤,骑一辆“小毛驴”,不仅重心不稳,还容易引来路人的侧目。更尴尬的是,万一被交警拦下,还得解释:“这位牛高马大的少年,真的刚小学毕业……”
开学第一周,据说按惯例不安排晚自习,正式的晚自习从第二周开始。听到这句话,我竟有些恍惚——
回想起自己的初中时代,晚自习这种事,至少要到高二才出现。我们那会儿,放学铃一响,书包一甩,就能冲出教室,一头扎进放学后的自由时光。
我又问了问几位九五后的同事,他们的初中也基本没有晚自习。
那么问题来了:从什么时候开始,初一就默认要有晚自习了?
更让我心头一紧的,是昨天听闻市里另一所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实验初中,有初一新生在报到当天就崩溃大哭。
开学第一天,语文、数学两门主科直接考试摸底,当晚就开始晚自习,一直上到晚上8:20。
走读生由家长接回家,住校生则要在9:30熄灯前完成三件事:
- 写完当天布置的作业
- 洗衣服
- 排队洗漱
对一群刚满12岁的孩子来说,这样的节奏未免太过严苛。
那一刻,我忽然意识到:美好的童年,其终点早已不是“毕业典礼”,而是“小升初”的那个暑假。
相比之下,汤总所在的这所初中还算宽松,主打“相对轻松的素质教育”。但即便如此,加上晚自习,每天在校时间也足足多了三个小时。若是赶上像最近CSP信息学集训这类特殊情况,一天在校时间甚至接近十二小时。
我不禁想:他们这一代孩子,究竟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?
课业的密度、节奏的紧绷、竞争的隐形起跑线……早已不是“努力”二字可以概括。
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,我们既无法为孩子铺就捷径,也无力改变大环境。
能做的,或许只是默默做好后勤,
在他疲惫时递上一碗热汤,
在他迷茫时充当一个愿意倾听的“知心大哥哥”或“大姐姐”。
——这微小的温暖,是我们唯一能握在手中的力量。